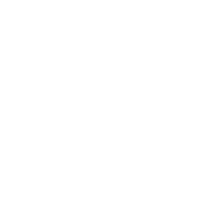
资讯


“那个朋友对你一定很重要吧,他怎么没跟着来?”林禾问。提起迟穗语,裴司尧的心猛地一揪:“嗯,但是她已经离开半年多了。”林禾身体一僵,看着裴司尧周身浓浓的悲伤顿时有些手足无措。“对不起,我口无遮拦勾起你的伤心事了。”裴司尧摇了摇头:“不怪你,是我自己把她弄丢了。”“什么东西丢了?”宋明浩从楼上走下来。洗干净的他褪去了刚才的柔美,多了几分少年人的刚毅,松垮的T恤也被他穿得意气风发。

刚从机场出来,他就被一个人撞了个满怀,摔在地上,就连手中的箱子都被摔了几米远。“谁他妈不长眼……”6裴司尧被撞的满身火气,张嘴就想骂人,却在看见怀里的人时哑了声音。那人穿着灰色长裙,身量纤细,抬眸时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人,看的人骨头都要酥了去。更重要的是她和迟穗语长得很像,唯一不同的只有那双楚楚可怜的桃花眼。迟穗语的眼睛是狭长勾人的狐狸眼,看人时总有种不自知的妩媚。

裴司尧把这个烧得遍体鳞伤的日记本带回了家。更加加倍刻苦地努力学习。短短六个月他就已经从年级末尾挤进年级前百,最后一次模拟考甚至考进了五十名内。进步速度令老师同学咋舌。就连林烟烟都对他转变了态度,不再是那副爱搭不理的模样。甚至主动在考完以后拦下他。“裴司尧,你这个学期很努力,如果你能和我考上同一所大学,我会履行去年的承诺和你在一起。”林烟烟说完这句话以后转身离开,似乎笃定裴司尧不会拒绝她。

他以为自己和迟穗语之间,主动权在自己身上,可是到如今他才发现原来他才是那个被动方。迟穗语离开了,他什么都不知道,甚至连她的QQ都联系不上。他对迟穗语的了解真的少的可怜,在脑海中仔细搜寻也只得出‘家境不错’四个字。他不知道她为什么一个人住在这里,不知道她父母在哪里,想找人竟也不知道该从哪里找起……裴司尧换了个姿势,把自己蜷缩在沙发里。挪动间似乎与有个粗粝坚硬的物体抵住了他的脖子。

“抱歉先生,我不知道......”女孩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答案,有些尴尬,但看着眼前这个落寞的男人,又很羡慕他和他妻子的感情。程煜笑笑,“没关系,她已经离开许久了,我也该走了。”女孩并不知道程煜口中的“该走了”是什么意思,只是简单的认为男人要开车离开了。只有程煜知道。这些日子,他所有的忙碌,都不过是在赎罪而已。关凛月在世的时候,他几乎从没对她好过,只有那一个星期的热汤,

程煜死死的盯着他,眼底只有恨意,语气却轻松。“你可以去告我啊,我又不害怕,只是这样你就会和我一样,失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血脉。”钱和儿子,就看虚伪了一生的程父会选哪一个了。“我要的不是当你的傀儡,我要你名下所有的股份。”程煜开始缓缓地绕着他转,目不转睛的盯着他的反应。“这三年来程衍在国外做的不错吧,就算失去国内的市场,你依然有一笔不少的养老钱。”或许是程煜的劝说起了效用,又或许是人老了,总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能留有传承,程父终于闭上眼睛。

程衍惊呆了,他看看帘子后面出现的白燃,又看看身前的程煜,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被耍了。“程煜,你竟然这样对我?!”程煜揣着兜走到他面前,“否则我该怎么对你,将你烧死,我再进监狱待个十年八年?”“亲爱的哥哥,你弟弟我虽然不是程家亲生的,但好像也没那么傻吧?”说完他掏出一直放在口袋里的右手,有一支录音笔正攥在他的手里。“你刚才说的话全都在这里,现在订婚宴该进行下一个节目了。”

周围的人们纷纷开始慌乱。“怎么了?这是什么情况?”“是不是停电了?”黑暗之中,程煜准确地抓起程衍的胳膊,强硬地将他的双手手腕绑起,直接带离了大厅。“你是谁?你快放开......唔唔......”程煜直接把一卷抹布塞进了程衍的嘴里,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的程衍,看见清了眼前熟悉的身影。三年未见,他这个弟弟比从前更加阴狠了。在确定是程煜之后,程衍不再发出任何声音,而是任由他拽着自己的胳膊往前走。

刚才那出闹剧之后,程父的身边少了许多上来吹捧和道贺的人,看着程父焦急的一杯一杯样自己嘴里灌酒,程煜的心里实在是痛快。就在这时,大厅的灯光忽然暗了下来,一束追光打在了楼梯上,程煜抬眼看去,白燃穿着一袭粉色的小晚礼,和一个男人手牵手出现在楼梯上。他的瞳孔晃了晃,那个男人就是他曾经以为的哥哥程衍。现如今的程衍,对比三年前多了几分华贵的气质,但眼底眉梢更多了几分如程父一样的算计阴狠。

这些媒体自然是程煜请来的,他给这些报道事实的新闻媒体编辑部都写了匿名信,告知他们订婚宴的详细时间和地点,并且将三年前发生的事,一五一十的在信上写明。他就是要让全城的人们都看到程家父子俩虚伪的面容。“这是怎么回事?把人都给我清出去!”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响起,程煜抬头看去,是白冉的父亲,也是白氏集团的总裁。程煜低声笑笑,这一幕也早就在他的预算之中。他自然知道程父没有能力抵抗流言蜚语,

说着,他将盒子递给宋晚霏:“这个就是头奖。”道谢后,那人就离开了。宋晚霏打开盒子,就见里面是一块翡翠,上面还刻着一个唐字。她不由地一僵。这快玉佩是已故外婆送给她的,但是后来被弟弟抢了过去,她三番五次想要要回来,都被父母给保了下来,再后来再去问,就被告知说是已经卖了。她找了很多年,一直没有找到。没想到居然流落到了m国,甚至还会成为一场非法赛车的头奖。她抬头看向icu里的男人,他就是为了这块玉佩,所以去赛车把自己弄进医院的?

就在她烦躁不已的时候,接到了医院的电话。“是宋小姐么?”“是,哪位?”“我们是中心医院的急诊中心,刚刚您的朋友江序先生被紧急送了过来,现在正在抢救之中,他唯一的联系人是您,所以需要您过来签字。”江序出事了?

“你不是不讨厌我?让我抱一下怎么了。”陆屿蹙眉,有些无奈:“你喝醉了。”“是啊,我喝醉了。”宋晚霏抬起红扑扑的脸蛋看向他,良久忽然伸手捧着他的脸颊,就凑了上去。“陆屿,我是一个很随便的女人,你怕不怕我现在就睡了你?”陆屿叹了一口气,掰开她的手:“我信,但你会后悔。”“不会。”“会。”陆屿将她打横抱起送到卧室的床上:“宋晚霏,你不是喜欢我,你只是因为江序的话受了刺激,想要证明,比起他耍了你,其实更像你耍了他,因为你除了和他睡,还能和其他的任何一个男人睡。”

江序连忙推开陆屿,就要朝着她跑过去,却被陆屿一把拽过,重重甩到了墙根。“江序,我警告你,不要再靠近晚霏,否则我会让警察将你遣送回国。”说罢,他大步上前牵着宋晚霏的手就向外走。上车后,陆屿帮她系好安全带:“今晚先睡我那,明天我重新给你找一间公寓,如果你不放心,也可以去酒店开个套房,或者……”“不用,就去你那吧。”宋晚霏低垂着头,心还是一阵阵刺痛。她不是难过看错了人,也不是依旧对他还有眷念,而是她竭力掩盖的伤痕,又再一次被江序扒开。

陆屿并不理会,按下电梯就走了进去。江序拦住电梯门,伸手去拽宋晚霏:“姐姐,别走,好不好?”说罢,他又冷冷看向陆屿:“放开她!她是我女朋友!”“那还真是巧了,我是晚霏的男朋友。”陆屿昂了昂头,右手随意地松了松领带,冷声道:“这位先生,痴汉并不能称之为男朋友,但你如果再缠着我女朋友,我会考虑报警。”举手投足之间全是成熟男人的魅力,不由地让宋晚霏有些看呆。“你说谁是痴汉?”

虽然心里早已放下,仇也报了,可江序的出现还是让宋晚霏有些烦躁。陆屿见她情绪不对,主动联系她,说晚上要和刘局通个电话,汇报一下最近状况。宋晚霏原本是打算去,可又担心江序还没走,便拒绝了。“暂时没有什么进展,你和刘局汇报就行了。”只是,她没想到,等她回到公寓,江序当真还在她的家门口。他垂眸靠在门边,一听到脚步声立马转头看了过来,见是她,立马勾唇笑了。“姐姐。”他轻声唤着,走到她的面前,摆出一副狗狗眼:“我没地方去,对这里又人生地不熟,姐姐可不可以收留我一晚?”

在全场起哄中,江念槐伸出自己的手。“我愿意。”顾韫砚如坠冰窟,无力地坐在看台上,一只手摁着头,眉心紧皱,脸色跟纸一样惨白。呼吸也带着急促,喉咙里发出‘嗬嗬’的声音。额头也有汗珠冒出,他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。他的目光紧紧锁在台下的两人,手更是死死攥紧,却什么都做不了。世间百般折磨,原来是在爱失去的时候。看着江念槐和祁天离开,他心如刀绞。夜色如墨,月洗铅华。顾韫砚走下看台,感觉自己的每一步都走的那么沉重。

他去了学校的后湖,这曾经是他和江念槐的秘密基地。但现在,只属于他一个人了。他坐在湖边平静地看着湖面,刚刚的画面不断地在他脑海里播放。还有室友的那句话,郎才女貌。顾韫砚感觉胸口好像有把刀,一直在扎自己的心,要扎破皮肉剜进心里。不然为什么心口会那么痛?江念槐和祁天般配?可明明站在江念槐身边的人该是他。想着,身边突然出现一道声音。“你还好吗?”顾韫砚吓了一跳,回头看竟然是江念槐。

他可以像上辈子那样,重新把她追到手的。下一瞬,他的心又坠了下去。江念槐的电脑壁纸是和祁天的合照。心中似有千万颗银针在扎。顾韫砚坐在江念槐的后面,像是一个小偷,偷窥着她的幸福。似乎是感受到他灼热的视线,江念槐回过头去看,他赶忙低下头去装作学习的样子。很快,江念槐就进入状态开始学习。顾韫砚只能小心的看她,想着自己该如何挽回这残破的局面。临近中午,他再一次去看向她的位置。

顾韫砚摆了摆手,只是怔怔的看着他们两个人。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,江念槐似乎和他成了陌生人,可明明不该是这样的。“我们走吧,食堂去晚了可就没你爱吃的猪脚饭了。”江念槐身边的男生说了他们见面的第一句话。他的语气很温柔,和他当初一样。“那我们就先去吃饭了。”临走前,江念槐还不忘礼貌的和他告别。是和记忆里一样温柔又美好的人,但她的身边已经站了别人。顾韫砚看着她离去的背影,心里的苦堪比黄连,从心底逐渐蔓延到四肢百骸。

面对佣人的疑惑,他直接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:“我找阿槐。”“阿槐?”佣人疑惑。顾韫砚看她模样,心里顿时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。“请问这里是江家吗?”顾韫砚不确定的问。“您找错了吧。”佣人否定,“我们家老爷姓祁,不姓江。”一句话激起千层浪,顾韫砚怔在原地。明明之前江家一直都住在这里的,怎么会变成祁家呢?难道是江家搬走了?“你们是新搬来的吗?”顾韫砚不死心的追问。佣人再次否定了他的想法:“我们家老爷在这住了几十年了,您是走错地方了吧?”